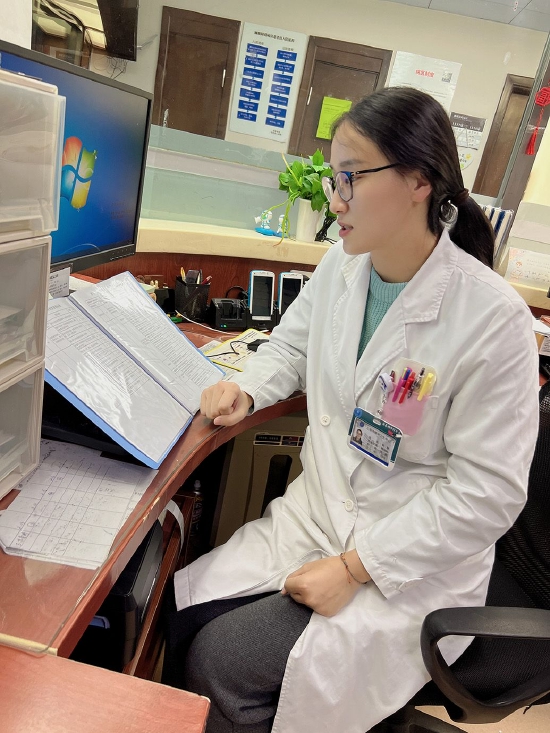|
孩子患上抑郁症,心理咨询师又去了精神卫生中心时间:2024-05-08 10:05 当小遥寻求帮助时,她遇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杨元带她去看了心理咨询,然后又去了心理健康中心。 小遥在电脑上做各种题,和医生聊天,最后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诊室外,杨媛隐约听到女儿跟咨询师说了几句话,然后哭得越来越大声。 杨元心里不舒服。 她之前就问过小遥是不是不高兴。 女儿什么也没说。 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工作的六年里,心理治疗师韩慧见过不少患有抑郁、焦虑、饮食失调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 他们的状态各不相同。 有些人与家人有冲突或难以适应人际交往。 有些人正在放假。 共同的特点是他们正在经历情感上的痛苦。 她还注意到,近年来,来经纬中心的青少年年龄越来越年轻化。 来经纬中心接受治疗的许多孩子只有11岁或12岁。 家长一般会根据孩子的行为来判断是否需要就医。 有些孩子到达医院时,已经表现出社交功能受损的迹象,比如不想上学、沉迷游戏、经常与父母发生冲突等。 当孩子的心理问题从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时,家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心理障碍的发生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称,任何时候,各种个人、家庭、社区和结构性因素都可能成为心理健康的保护性或破坏性因素,包括情绪技能、遗传等。面临包括贫困在内的不利环境的人、暴力、残疾和不平等等风险很高。 对于某些心理疾病,例如抑郁,经历不良生活事件可能会让您面临更大的风险。 2020年9月,山西一名高中一年级女孩林琳开学后不久就告诉妈妈方轩,她不想再上学了。 那天,林林与学校老师发生了冲突,成为压力和情绪的导火索。 她躲在厕所里给方轩打电话,边说边哭。 方轩在电话里听到了老师喊孩子们的声音。 接下来会出现一些症状。 那段时间,林琳经常出现头痛、胃痛、不明原因发烧、失眠等症状。 在医学上,这些表现被称为躯体化,是指负面情绪或心理障碍转化为躯体症状。 方轩带着女儿去了医院,做了很多检查,除了鼻炎、腰椎间盘突出,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在亲戚的提醒下,她和琳琳去看了心理咨询。 辅导员告诉方轩,林林患有严重的抑郁。 2020年11月,林琳开始请假在家休息。 新年过后,方轩去学校申请休学。 漫长的诊断和治疗 有时,小遥一个人坐着,低着头,一言不发,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严重时还会出现更明显的身体反应,如手抖、胃痛等。 被诊断出患有严重抑郁后,小遥开始每天服用精神药物。 前两周,杨元无法忍受药物反应,小遥精神也不佳,经常感到恶心、头晕。 但杨远连担心药物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的机会都没有。 “到时候只能吃药了,不吃药怎么办?” 与此同时,杨元坚持带小遥进行心理咨询,密集期每周两次。 。 2021年6月,小遥参加了学校的期末考试。 暑假期间,杨元没有要求她做任何作业,只是在家休息。 九月初的第二次早自习结束后,小遥就回家了。 暑假期间她没有预习,听不懂课,但同学们似乎都听懂了。 10月,杨元正式帮她休学。 当她和女儿去学校请假时,班主任建议她们再考虑一下。 他说,如果继续上学,可以和每个老师达成协议,不要求孩子完成作业。 他还鼓励孩子们只要坚持上课,升学就没有问题。 逍遥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哭。 杨元毫不犹豫,坚持休学,“我只想孩子健康快乐,别的什么都不想要”。 但另一方面,她又陷入了迷茫和无助。 为什么她吃了快四个月的药,看了无数次的心理咨询 ,孩子还这么痛苦吗? 精神疾病的康复周期通常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 韩慧在医院临床心理住院病房担任心理治疗师。 这里住院的一些孩子患有饮食失调、强迫症、抑郁疾病。 不同类型问题的患者住院时间是不同的。 饮食失调患者的住院时间一般为两到三个月左右,抑郁、焦虑患者的住院时间一般为一两个月左右。 但出院并不意味着完全康复。 以抑郁为例,抑郁科普平台及康复社区“嘟嘟”发布的《2022青少年抑郁功能恢复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患者在抑郁发作后,伴有残留症状和社会功能受损。 受复发、残留症状等因素影响,抑郁往往会变得更加慢性。 在“嘟嘟”调查中,近50%的青少年患者病程超过2年,其中约10%持续时间超过5年。 此外,调查中超过一半的患者出现过复发,其中约22%的患者复发次数超过3次。 韩慧见过住院两三次的患者,有的出院一周后又回到病房,但她对“复发”的定义比较谨慎。 “也许他觉得自己快康复了,想出去尝试一下,但实际上他还没有准备好,回家后感觉不安全。” 她解释说,“对于精神疾病有一种不确定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起来。也许这让我更加焦虑。” 她注意到,很多回到病房的患者和家属都会有心理负担,担心是否还要再做一次。 有些人会调整心态,说没关系,“但悲伤还在”。
上海经纬中心,??韩辉在工作。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家庭反思 一些人认为,家庭应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承担主要责任。 但韩绘也理解家庭的不易。 “家庭会对每个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不认为它是决定性的,也不是大多数。人类是多样化的生物,除了家庭之外,还要接触外面的世界(环境)、社会、学校。” ”。 她说,一些家长已经完全暂停工作,留在医院陪伴孩子,让孩子慢慢好起来。 家庭是支持青少年度过考验的关键。 在医院,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常常结合起来。 住院期间,医院提供多种形式的团体辅导,如游戏、艺术治疗、认知行为治疗、辩证行为治疗等,韩慧所在的病房允许家长陪同。 陪床陪孩子学习课程并进行家庭治疗的家长。 一些青少年的症状更常在家庭中表现出来。 韩惠遇到一个10岁的女孩,她不与家人沟通,不愿意上学,洗澡、吃饭都非常被动。 当父母送她去医院时,女孩没有说一句话。 她觉得孩子挺严重的,似乎沟通、日常生活等社会功能都受损了。 但没想到,女孩一个人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慢慢开始说话,和同院的朋友玩游戏,变得相当外向。 从女孩的话中,韩绘了解到女孩的父母之间矛盾很大,经常有不同的意见。 她给女孩的父母进行家庭治疗,发现两人总是情不自禁地互相指责。 韩绘直言不讳地对家长们说:“如果我是你们的孩子,此刻我会感到呼吸困难。” “父母不同意,孩子最后不肯说话,我该帮谁呢?但她离开家庭环境后,病房里孩子很多,她发展出了纯真的友谊,可以玩游戏,环境不一样了。” “她好像正在慢慢起死回生。”韩绘说道。 女孩在医院住了一个月,韩绘给她父母做了四次家庭治疗。 后来,这对夫妇意识到他们不断的争吵以及这对他们的孩子造成的影响。 渐渐地,他们的矛盾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之间隐藏着很深的情感,四次咨询肯定是不够的。但他们确实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至少在孩子面前。”韩惠说。 直到女儿琳琳确诊一段时间后,方轩才明白了孩子之前行为的意义。 初二的时候,林林经常用笔在手腕上画画,做出分裂的效果。 心理咨询告诉方轩,孩子早就有自杀的念头,幸好他们及时赶到。 方轩寻找着孩子生病的原因,回忆着与孩子相处的每一个细节。 林林的成绩中等。 他曾说过,从小学开始就不喜欢上学,但他安静、听话、懂事。 高中时,琳琳对科目非常偏爱。 高一英语得满分,数学却只得20分。 方轩不问成绩,但丈夫严厉,从琳琳小学开始就打骂孩子读书。 当方轩因诊断出抑郁提出休学时,丈夫仍然不同意。 他脾气暴躁,让他的孩子必须去上学。 “孩子说他想死,父亲说你去死吧,然后摔门走了。”方轩说道。 方轩逐渐意识到,父母之间的矛盾、亲子之间沟通不畅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伤害。 她想起一件事。 有一次,琳琳想和全家人一起去旅行。 方轩的丈夫想去,但因为工作抽不出时间,一直拖着不给孩子回信。 孩子有些不高兴,方轩就去问他。 丈夫被逼入绝境,夫妻俩发生争吵。 琳琳哭着说道:“如果你不生我,你还会有这些东西吗?你为什么要生我?” 辅导员告诉方轩,对于孩子来说,吃药、住院、咨询只是辅助手段。 只有父母改变自己,孩子才能真正变得更好。
林林拍摄的日落 方萱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来了解情绪的发生和处理,并希望影响和改变丈夫。 当她和丈夫发生矛盾时,她先肯定丈夫好的一面,然后再讨论具体问题。 为了帮助丈夫更好地了解抑郁,她在网上找到了科普视频。 当丈夫与孩子沟通时,她将谈话录音并播放给丈夫听,让他知道沟通问题出在哪里。 让方轩松了一口气的是,她的丈夫听了录音,说他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 他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 孩子们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前犹豫不决 在九年一贯制学校担任心理老师的陆青曾经期望学生主动去心理咨询室咨询,但她的期望并没有得到满足。 有时一两周都没有学生来。 另一所学校的心理老师刘奇也看到过很多犹豫不决的孩子。 他认为,有些孩子想寻求帮助,但心里有障碍。 他习惯于直接与学生进行安排,告诉他们谈话是保密的。 有的学生听完,会主动挽起袖子,露出小臂上被利器划出的伤痕。 孩子往往不轻易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需要周围人更多的关注。 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需要各方反思和行动。 有专家认为,家长的期望、升学的竞争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给儿童青少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兴奋和心理压力。 成都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孟红琴介绍,家庭最终最有可能为孩子建立健康的成长体系。 “父母必须理解他们的孩子,这样他们才能感到安全和强大。” 患有精神疾病 向他人解释精神疾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起初,方轩甚至没有告诉女儿诊断结果。 “那时候,孩子们都会自责,认为既然别人都去上学了,我不去就不好了。我告诉孩子们的是,我们选错了学校,如果你不去,那就不好了。”像这样的教育环境,我们就应该在家学习。” 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不久,方轩上高一的女儿林琳表示不想再上学,并出现头痛、失眠等不明原因症状。 她被诊断出患有严重抑郁,随后停学在家接受治疗。 方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和女儿的经历,不少家长纷纷留言和私信,诉说着她类似的困难。 后来,她和其他家长建立了联系,大家互相分享孩子的现状和心理相关知识。 “大家都认为抑郁是一种精神疾病,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没有人倾诉。这里的每个人都一样,不怕别人笑,能互相理解、互相帮助。” ,“ 她说。 一位家长曾告诉她,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她女儿抑郁,并以此为由羞辱孩子、讨厌她。 “我们的社会不理解、不重视、甚至鄙视抑郁。 这让很多想要回归集体的孩子望而却步。 希望大家能够对孩子有更多的理解、支持和温暖。 很多抑郁厌学的孩子都是优秀的孩子,只是有点敏感而已。 他们想要的是被尊重,而不是同情,不是厌恶。”方轩说道。 开学之际,有妈妈在群里分享了孩子返校的经历:孩子连续三天准时到校; 今天他们比昨天走得早,孩子们也不想迟到; 老师打电话说他们的孩子状况良好。 对于家长来说,复学是个好消息,但也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 休学半年,林林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 躺下后他很快就能入睡,饮食也开始更有规律。 他的躯体化症状也改善了很多。 他的头痛和胃痛减轻了,有时还要求出去。 她向方轩提出想学画画。 2021年夏天,方轩找到了老师给林琳补课。 随后,林琳只身前往北京的一家工作室接受训练。
从北京回家过年的火车上,林琳拍下了风景。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方轩心里有些高兴,但也有些担心。 琳琳回家玩手机,老公就会唠叨她,认为孩子没有进步。 方轩指出,他可以停几天,但过了几天他又会焦虑。 在读初中的小遥退学之前,杨远就已经想到她以后一定会复学。 但当小遥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她也想到了自己可以退学了。 她和丈夫愿意继续抚养女儿。 2021年5月,在杨远眼里似乎没什么异常的小遥突然说道:“妈妈,你帮我找个心理医生吧。” 之后,她被诊断出患有严重抑郁 经过治疗,小遥在2022年夏天被诊断出患有轻度抑郁。9月份,杨元为小遥恢复学业做了很多准备。 她提前去找心理咨询进行心理疏导,并准备了急救药品。 在杨远的要求下,逍遥从原来的重点班转到了平行班。 回到学校的第一个月,小遥起床后偶尔会感到不舒服,胸闷气短。 她对学校感到焦虑和紧张,每周不得不休息一两天。 杨媛从来不离开手机,生怕老师打电话。 她不敢去想,如果去年的情况再发生一次,她会怎么办。 幸运的是,小遥参加了10月份的月考,数学没能考完,但她的成绩却在年级里上升了100多位。 在平行班里,小遥的压力得到了缓解,她也结识了好朋友。 身体不好的时候,杨媛要求老师不要交作业,偶尔也会帮女儿做作业。 小遥紧张的时候,她就通过各种方式让孩子玩游戏、看电视来放松。 此后,小遥几乎没有再请过假,平安顺利地度过了整个学期。 犹豫的孩子 除了家庭之外,学校是青少年长期生活的另一个环境,其中包括同伴和老师。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坚持发展、预防和危机干预相结合。 但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及早发现需要外部支持的孩子呢? 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在严重问题出现之前获得帮助? 每天中午,陆清都会在心理咨询室等待。 2020年,她开始在上海一所九年制私立学校担任心理老师。 学校给心理咨询室规定了固定的开放时间,选择每天午休时间一小时。 为了让学生知道心理咨询室开放了,陆清每次都会在课堂上宣布。 在她看来,每天中午接待一个孩子一小时是最合适的。 然而,主动咨询的孩子比她预想的要少得多,有时一两周都没有学生来。 她不明白问题的关键,猜测原因可能是孩子忙着吃饭、午休,也对心理老师缺乏信任。 上海另一所学校的心理老师刘奇看到很多孩子在向外界寻求帮助时犹豫不决。 有的会在上课的时候到咨询室看一下,有的则二话不说就过来测试一下。 为了调查学生的心理状况,刘奇所在的学校会在返校前、考试前、网课期间等特定时间点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问卷列出了有关学习压力、同伴互动、睡眠和饮食状况等十多个问题供学生评分。 但在刘奇看来,问卷在鼓励学生寻求帮助方面的意义大于其筛选和监测的意义。 在问卷中,学生可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一名初三男生在填写问卷时,对自己的睡眠状态给出了最低分。 刘奇主动邀请他去办公室聊天,男孩三四次都没能预约到。 刘奇邀请他一起去散步,聊聊学业,但男孩还是没怎么说话。 直到第三次聊天,男孩才说出了他的烦恼和状况不佳的一些原因:他以前的好同学已经转学到另一所学校了,现在他没有人可以倾诉他的烦恼。 学生的犹豫是可以解释的。 刘奇认为,学生想要寻求帮助,但存在障碍。 比如,他们担心心理咨询会意味着自己心智不好,或者会影响学习,或者担心自己在同龄人心目中的形象。 他有一个直接同意学生的习惯,即除了自残、自杀或严重犯罪行为外,谈话内容是完全保密的。 有的学生听完,会主动挽起袖子,露出小臂上被利器划出的伤痕。 他认为行为表达比较模糊,需要直接告诉孩子,“最好让学生毫不犹豫地走进咨询室”。 成都市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委员、成都市石狮天府中学心理准备小组组长孟红琴认为,问卷筛查是“不得已”的方法,效果有限。 学生的心理状态是不断变化的。 调查问卷可能会在9月进行,但无法知道学生在12月是否遇到麻烦。 他说,真正能及时发现、及时预警的,其实是那些日夜与学生相处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他们其实很了解孩子。 他说,“当一个人心情很低落的时候,难免他的情绪会写在脸上。” 这一观点已得到证实。 有一次,高三年级的孟红琴上课时,发现一名学生表情奇怪,“有点失望”。 下课后,他问她大部分学生都离开后发生了什么。 学生泪流满面,却摇摇头,不愿说话。 他说,如果你遇到什么难以面对的事情,可以来找我,好吗? 学生点点头。 “如果没有人这么说,她可能会陷入危机(案件),但当我这么说时,她知道她可以先尝试和我谈谈,”他说。 他介绍,成都市还计划在班级开展同伴心理辅导,并在每个班级设立心理委员,及时关注学生动态。 他知道有一次,有同学发现有学生不去吃饭,就及时通知了老师。 最终,这名学生被从学校高栏杆上救了出来。 社会“事业” 心理工作者也有“无力”的时刻。 比如,班主任把一个不做作业的学生带到心理咨询室,希望路清立即解决问题,劝他学习。 另一位心理老师表示,她的学校有2000名学生,配备了一名心理老师。 面对某些情况,学校能做的很少,比如学业竞争、内卷化环境中的压力等。 孟洪钦曾对学校领导表示,他不认为分数可以用来评价学生。 学校领导说,小孟,你太理想了。 “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欣赏度没有任何联系。至少家长必须明白这个观点。如果哪个学校能做到,就不会用这么一维的指标来评价学生,真正看到每个学生的优点。” “学生的特点,让他快乐,事实上,这可能反过来提高他的学习成绩。”孟红琴说。 他认同心理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这一观点。 比如,中小学教育似乎就建立了这样一个逻辑——考上好学校,拿到好文凭,找到好工作,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有时听到网上“赚钱很重要”之类的言论,他会感到不舒服。 这种逻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 一名学生告诉孟红琴,他觉得父母并不爱他,只爱考试得高分的人。 心理治疗师韩辉也曾见过患有强迫症的青少年。 他们害怕“成为乞丐”,因为考不上重点高中。 一些沉迷游戏的孩子告诉她,他们对学习没有信心,没有成就感,所以就玩手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教授、儿童精神病学首席专家郑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独生子女问题日益突出。 、网络成瘾等正在影响着家庭和社会。 家长的高期望、学习的压力、升学的竞争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给儿童青少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兴奋和心理压力。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问题,我不建议我们把重点放在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上。我认为更多的力量应该放在如何帮助一个普通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上。” 孟红钦说道。 他还指出,“如果(心理学)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家庭往往也是‘受害者’。但如果说谁最有可能建立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体系,那确实是家庭。家长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孩子,这样孩子才会(感到)安全、有力量。” 杨媛并不是“鸡宝宝”的家长,但她回忆,小遥进入初中重点班后,不经意间对孩子的成绩名列前茅或垫底表示出暗暗的喜悦或失望,这可能伤害了她孩子。 后来逍遥告诉她,她不会允许自己不够优秀。 2023年2月中旬开学,小遥将进入初中最后一个学期。 中考临近,杨元慧和所有家长一样,希望女儿能考上一所好高中,选一所好大学。 但她时常回想起去年复学时的心情,“万一进了好高中,又旧病复发或者不舒服怎么办?高中的压力是初中的压力无法比拟的。” 小遥的学习任务还有很多。 焦虑,有时进校门前需要深呼吸。 杨远想了想,道:“去普通高中就可以了。” (为保护隐私,除韩辉、孟红琴外,其他受访者均为化名) 记者何佩云 如果遇到心理困扰,可以随时联系爱己心理,遇见爱己,开始爱己 |